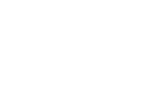王绶琯院士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所著序言
来源:发布时间:2021-03-23
编者按: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在23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发出了著名“天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观察和探究宇宙的奥秘。公元前十三世纪甚至更早,中华民族的先人就建立了天文台,中国至今仍保存着世界上历时最长、最完整的天象记录。近百年前,中国现代天文学开始起步,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1928年中国第一个现代天文研究所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陆续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化天文台站运行体系,1958年,国家天文台的前身——北京天文台应运而生。2001年,为凝练我国天文科技目标、调整天文学科技布局,中国科学院决定在原天文台系统的“五台三站一中心”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组建20周年。20年披荆斩棘、风雨兼程,国家天文台已发展成为集天文学基础前沿研究、天文技术方法创新及应用、重大观测装置建造与运行、国家月球与深空探测科学应用和国家空间碎片监测与应用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国立天文研究机构,成为中国天文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回顾国家天文台的发展历程,老一辈天文学家爱国、奉献、治学、修身的风骨,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谋划,以及为建设国际一流天文台的不懈努力,依然历历在目……值此国家天文台迎接组建20周年的日子里,将王绶琯院士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撰写的序文在本网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史(1958-2001)
序 王绶琯(2006年)
北京天文台(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并未进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龄”不足50年,看起来似颇短促。但如果用历史的时间尺度来度量,它还是在中华古国文明的道路上走过了百分之一的路程,而同一时期郑世聪“大跃进”到“调整巩固”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大动荡、大变迁。准确描绘这一段时代背景恐怕需要的是一两代历史学家的努力。而这样的背景下,受其影响,一项事业、一个机构,乃至一个人的经历同样是跌宕起伏,难以写真。可以举一个例子:北京天文台最早的工作基地——沙河工作站。它一开始的两间竹板房是北京天文台的第一个实验室,启动了射电天文建设;接着按原计划在那里建了“时间服务”,后来又添上了“人造卫星服务”;继而全台各门学科陆续进驻沙河站,使它一度成为繁忙的临时“大本营”,好几个业务团队在此“整军待发”;“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却变成了一所“牛棚”;而今天这一切都已经消失,雄踞在那里的是一座颇为气派的私立寄宿学校,不过在一个角落里还留有几间屋子见证“天文学的产业化”。还有一个展室,展现了这个小小天文单位的“文物化”。真可谓几度沧桑!
当然,这种沧桑是“正道”、是整体进步的局部反映。而举这个例子可以表明,为这样一个工作站写出有骨有肉的历史显然绝非易事。这不但是因为“历史地”理解这些“沧桑”,或把这些“沧桑”置入历史的框架要掌握更多的资料、需要下更大的历史学工夫,而且因为这“一沧”和“一桑”之间的历史资料会更容易湮没,而实际上是不断地在湮没!
当然,沙河站的情况并非孤立,天文台的其他部分也各有各的“沧桑或“桑沧”。写出一部北京天文台50年里创业的艰辛和发展的曲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历史当然不能不写。这些困难只是说明写这样一部历史不能一蹴而就,既必须为分析历史背景的影响留出更多的滞后时间,又必须面对资料任务的繁重,尤其是许多资料已经湮没的事实。于是北京天文台台史的编者们决定尽早动手,先把史实的掌握提上日程。
实际上,掌握史实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再以沙河站为例:从最初建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工作站先后有五位负责人(编者按:即俞文祯、史润兰、赵瑞盛、韩锡三、梁学增),他们如今均已作古;而在那里,足以标志当年一个天文学基地的实物,大部分已经了无痕迹。
历史,大到一个朝代的正史,小到一个人的传记,总是要分为两个步骤来处理的:首先是见证者的实录,然后是治史者的著述。著述实质上是历史研究,不必拘于一家之手。而实录则有赖于见证者的求实、求真、“细大不捐”。历史研究是长期的,而实物的或文字的、自制的或偶成的实录,则是构成历史的细胞。今天我们关注的北京天文台历史,首先应当是这近50年间见证到的实录。
回顾20世纪,北京天文台,当年作为我国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产物,在我国近代天文学史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北京天文台的工作同志有责任为我国天文学界记录好、保存好、整理好,以及(后继的)搜集好北京天文台创业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实录。在档案文献多有缺失的情况下,台史的编者把完成这个任务的希望寄托在当年当事者的回忆上。于是就有了这部史稿。
这些当事的“老同志”今天都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们不负所望,以老同志特有的认真负责,完成了使命。书稿按类分篇,分题列条。虽然长短疏密各有风格,但是每读完一篇,都会唤回一部分不应忘却的记忆,这是令人感慰的。
这种分题列条的方式,是“储存”资料最合理的办法。这50年里人与事的变迁中有许多突变和间断,但是业务研究,也就是各门分支学科方面的实录,却都基本上维持了“历史的连贯性”。这应当归功于这方面的“人”大多数没有随着“事”变,因而这一部分实录可以说是为历史资料的继续发掘和历史得失的研讨准备好了很好的基础。
与之对照,全局性建设和行政管理方面这大多是“人随事迁”,实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层以至缺失。其中时间愈久的就愈严重。这使得创业期间材料的搜集变得格外困难。史稿中把焦点聚集到北京天文台的两位奠基人——第一任台长程茂兰和第一任党委书记肖光甲的“生平”追记上。这应该说是对创业阶段的台史做了最有代表性的实录,唤回的更是一些不应淡忘的记忆:程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天文台的筹建是当年党的科学政策的体现。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程先生没有亲身实现他对北京天文台建设的愿景,但是他在我国首次引进了现代天体物理观测基地的蓝图,并具体为台址、设备规模和人生共同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台—系紧密合作的天体物理专业。这些首创,其影响都跨越了“断层”,浸透在北京天文台的历史全程中。同样,肖光甲同志负责执行党的政策,在完成了从零到初具规模的设备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为北京天文台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切实的基础。围绕这两篇“生平”的事迹,将可望发掘到更多的史料,而这些事迹和史料的回归,将有裨益于北京天文台总史的完整度和可溯性。
记得建台之处,程茂兰先生曾经时时带着他的手携摄像机在各种场合摄下影像,随时积累北京天文台建设的记录。可惜在后来的动荡年月里人们普遍失去了这种从容,而大家也始终未能延续程先生的这一倡导。今天这部史稿的诞生,或许也可以稍报程先生的这一初愿。
(编辑:黄京一)
- 附件下载
-